〈建築理論研究 06〉──篠原一男『住宅論』『続住宅論』 , from from 《10+1 website》建築理論研究会 , conversation with 坂牛卓(特別來賓)+南泰裕+天內大樹

〈建築理論研究 06〉──篠原一男『住宅論』『続住宅論』 , from from 《10+1 website》建築理論研究会 , conversation with 坂牛卓(特別來賓)+南泰裕+天內大樹
原文出處https://www.10plus1.jp/monthly/2014/09/-06.php
(版權聲明:本文摘錄於10+1 website,版權歸屬:© 2000-2020 LIXIL Corporation/本翻譯為自行完成,僅供學術研究和非商業用途使用。如有翻譯不當之處,敬請見諒。翻譯:陳冠宏/校稿:徐榕聲/翻譯協助:ChatGPT 智慧之光/附圖:《地。-關於地球的運動-》)
〈建築理論研究 06〉──篠原一男《住宅論》《続住宅論》
坂牛卓(特別來賓)+南泰裕+天內大樹
與社會對峙的手段
天內大樹──這個系列雖然以「建築理論研究」為名,但所謂的理論,是一種可以在紙上構築、較容易由自己控制的事物。另一方面,圍繞當今建築的狀況,如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便以「Bigness(ビッグネス)」的概念將其正面地敘述出來,這樣的規模預設了超出單一建築師能夠掌控的範圍。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定位「理論」的角色?這正是啟動本企劃時我們最初關注的議題之一。
這次要探討的篠原一男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正是透過住宅這一類型,建築師才能與社會對峙,對社會進行批評。像是「白之家」(1966)或「傘之家」(1961)等個別作品中,這樣的觀點也有所體現。與我們前回探討的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不同,羅西是透過公共建築或複合設施等方式,將他作為建築創作者的理念向社會展開;而篠原先生所處理的,則是規模小得多的住宅空間。以這樣的住宅為槓桿,實現創作者與社會的對峙。
篠原先生的思想,看起來像是建築師逐步從都市與社會中退卻的過程;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視為建築師所能做之事逐漸被限縮的開端,並與當今的狀況有所連結。
今天我們邀請到曾直接受教於篠原先生的坂牛卓先生,自然想從住宅的角度開始請教您。在當下的時代,透過建造住宅來與社會對峙,這樣的事是否仍然可能?亦或是坂牛先生您自己,在設計住宅時是否有意識到這樣的立場呢?
坂牛卓──我確實是從篠原先生那裡學習建築的,不過到了某個時期,也開始有一些像是「反面教材」式的思考出現。大學畢業後,我進入日建設計,而在那之前,我曾向伊東豊雄先生請教。當時正值伊東先生完成「Silver Hut」(1984)不久,我對他說出了一句很自以為是的話:「設計住宅對社會真的有什麼影響嗎?」結果他非常生氣地回我:「一棟住宅當然能夠改變整個社會啊!」這當然是理所當然的事,篠原先生也是這樣想的。
篠原先生常說:「若住宅建築未能透過照片在社會中流通,那它就等於不存在。(住宅建築というものは写真になって社会に流布しないと存在しないも同じだ)」也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強烈的視覺性與攝影表現力。不過,這樣的理路在今日是否仍然適用?恐怕就難說了。篠原先生從事住宅設計的時代,會以「建築」之姿來設計住宅的人寥寥無幾。反觀現在,像是《新建築》也有《住宅特集》這樣的刊物,一般雜誌中流通著大量住宅影像。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張照片所能帶來的衝擊力,恐怕已不如當年。
天內──那麼,坂牛先生您自己在設計住宅時,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感受呢?
坂牛──將我自己與篠原先生相比或許沒有太大意義,但「住宅是各種建築精髓的集大成」,這一點可以說是我們之間的共識。透過住宅,我可以凝縮地實踐我想在建築中實現的事物,而這些觀念也可以進一步應用到其他類型的建築中。這樣的認知至今仍未改變。
在我還沒進入大學時,篠原先生與磯崎新先生據說曾一起舉辦讀書會。那應該是因為兩人有著相近的追求。不過,我想當時兩人都已開始有「都市變得難以掌握」的感受。磯崎先生原本就是以都市為主題,卻在某個時期開始逐步撤退。篠原先生應該也曾對都市懷抱興趣,但未曾深入,最終也選擇抽身。
然而到了1980年代,篠原先生又重新提出「都市之美存在於混沌之中(都市の美はカオスにある)」的說法。他希望將「混沌之美(カオスの美)」與自身的設計工作結合起來。我想「東京工業大學百年紀念館」(1987)正是這樣的嘗試之一。雖然最終未能完工,但像「蓼科的別墅(蓼科の別荘)」這樣的作品,留下了多達700張草圖──也成為《篠原一男》(TOTO出版,1996)的封面──可說近乎混沌。我認為這也是一種將都市混沌之美延續到住宅設計的實驗。
天內──原來如此。那麼,當篠原先生說「透過住宅與社會對峙(住宅によって社会と対峙する)」時,他所設想的主體,是建築家嗎?還是業主?
坂牛──那當然是建築家。篠原先生曾說,設計建築時,業主與基地條件都無關。他認為若預算低就蓋不出好建築,或因基地不佳就無法創造好建築,這樣的說法對建築師而言是太不負責任了。這表示,在他的前提中,業主並不會直接介入建築師所要設計的東西。這點和我們這一代人是很不同的。
天內──也就是說,與坂牛先生您自身的立場是不同的。
坂牛──關於「私」這個概念,我認為從坂本一成先生那一代開始就已經有所不同了。坂本先生的「散田之家」(1969)與篠原先生的「白之家」同樣是在60年代後半期建造,但處處可見其意圖在於如何修正「白之家」那些令人難以接受之處。儘管「白之家」與其平面幾乎一樣,但一旦走進「散田之家」,感受卻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說,這棟住宅簡直就是將白之家脫胎換骨為目的而建。對坂本先生而言,篠原先生當然是老師,但我覺得其中也包含了一種反面教材式的影響。據說,當出身篠原研究室的武田光史先生參觀坂本先生的「代田的町家」(1976)時,曾說過「這棟建築裡沒有空間(この建物には空間がない)」這樣的話。不過我認為,坂本先生本來就是有意為之。另一方面,在篠原先生的住宅中,常常是封閉的白色盒體,沒有任何空隙。換句話說,那正是所謂的「有空間」。
再回到社會的脈絡來看,進入70年代後,大家一度從社會性的事物中撤退,但之後又逐步回歸,如我剛才所提到的。篠原先生後來開始在建築中尋求「混沌之美」,而坂本先生則從最初強調「乾燥的空間」而創造封閉空間,慢慢地也開始將空間向社會開放。我認為伊東先生在某個時期以前,也是在與坂本先生相似的頻率中進行建築創作。例如,坂本先生的「project KO」(1984),如果看模型就會發現它沒有牆面,是一個空間貫穿的設計,這在我們看來與同年建成的伊東先生的「Silver Hut」(1984)是相互呼應的。進一步說,這也許是一種表明:即便是住宅規模的建築,也能與城市連結、延續的意志表達。
南泰裕──《住宅論》在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已經幾乎成為一本傳說中的書籍。篠原先生本人也逐漸接近一種傳奇般的存在,當時他已經在談論「混沌」或「隨機性」這些概念。從60年代到70年代,先生設計了大量強烈密集的住宅,並將其總結成《住宅論》,而且書中所寫內容極為激進,我們當時讀了都非常震驚。我想,對於非東京工業大學體系出身的人來說,這種神話化作用也許更為強烈。
然而,這次我重新閱讀那本書,竟然覺得它所寫的其實非常正當合理。無論是「住宅是藝術(住宅は芸術である)」這樣的發言,或是「住宅越寬敞越好(住まいは広ければ広いほどいい)」、「用地與建築無關(敷地は関係ない)」之類的說法,若是單獨抽出來看,的確容易讓人覺得傲慢、自我中心、像個藝術家。但如果通篇重讀,會發現其實非常合理。在我看來,篠原先生是一位極為理性的合理主義者,完全不像是所謂的創作者。甚至可以說,他也不像是專門的住宅建築家。我覺得,他只是作為一名建築師從事建築工作,而剛好從事了住宅設計而已。所以,那本書若不是叫《住宅論》,改叫《建築論》也絲毫不違和。儘管人們對他有一種超然脫俗、不隨時流的孤高建築家印象,但實際上他廣泛談論了當時建築界面臨的各種課題,包括預鑄建築(prefabrication)、代謝派(Metabolism)等。從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也就是從韓戰到大阪萬博這段高度經濟成長的時代,他清楚觀察建築所處的環境,並以普遍性的觀點論述建築。
在此基礎上,我想進一步思考當下閱讀這本書的意義。目前在埼玉縣立近代美術館正舉辦「戰後日本住宅傳說(戦後日本住宅伝説)」展(2014年7月5日至8月31日),展中也展出了篠原先生的「白之家」等作品,「傳說」這個詞被寫進展覽標題本身就是個象徵。我們這一代人也參與了這個傳說化的過程,我認為這其中有功也有過。或許我們把一些原本不需要被神話化的事物也變成了傳說。這次我重新翻看篠原先生的作品集,發現他經常進行一種操作:將不是作品的東西作品化,或是巧妙地讓不想被看見的東西不被看見。我也曾親身參觀過這次「戰後日本住宅傳說」展中展出的一些住宅,對篠原先生在建築世界中所達成的、他人從未實現的成就,當然充滿敬意;但同時,我也必須承認其中確實存在著某種不必要的神話化作用。因此,我們現在也許需要對這種神話作用進行「脫色」的處理,不是嗎?

「戦後日本住宅伝説」展

篠原一男『住宅建築』(紀伊国屋書店、1964)
坂牛──比起《住宅論》,篠原先生其實早在六年前的1964年就出版了《住宅建築》這本書。事實上,《住宅論》中所收錄的絕大多數論文,都是在1964年以前完成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住宅論》還是《續住宅論》,其實都是從不同比例的時代與論述中,嚴選出來所編成的。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才讓這些書的體裁顯得如此合情合理、具有說服力。
南先生剛才提到篠原先生是個很「合理」的人,我完全認同。畢竟篠原先生原本就是學數學出身的,對那些不合邏輯的說法,他是無法接受的。但也正因如此,他的身上又帶有某種刻意偏離常理的「偏執性」,那也正是他個人魅力的來源之一。我想坂本先生會說「篠原先生到頭來還是個詩人(結局、篠原さんは詩人だよね)」,應該就是在指這一點吧。
南──是啊,我也有同感。昨天我去看了「戰後日本住宅傳說」展時就有這種感覺。像是「白之家」這件作品,它其實並不是柱樑結構。平坦的天花板下方,並沒有作為水平構件的梁貫穿其中,而是有看不見的斜向構件在動態地支撐著屋頂的架構。因此,整體來看,並不是傳統的軸組結構,確實帶有某種偏執性的特質。
之所以會覺得《住宅論》具備某種邏輯上的一致性,也許是因為篠原先生的寫作中充滿了「反制」或「反語」的語氣。比方說,當池邊陽提出〈立體最小限住宅(立体最小限住宅)〉並說「住宅越小越好(住宅は狭ければ狭いほどいい)」的時候,篠原先生就反過來說「住宅越寬敞越好」。他總是說出與主流觀點相反的話。然而,奇妙的是,我們往往反而覺得篠原先生說的才是「正道」。與其說是機能主義者或代謝派那些自稱「積極參與社會」的建築師,倒不如說他們其實抓不到現實的細膩之處,常讓人覺得有所偏差。
例如在《續住宅論》中收錄的〈都市與住宅的「封閉系統」(都市と住宅のための〈閉じた系〉)〉這篇論考中,篠原先生提到:「許多進步的設計師與理論家皆主張設計應具有對社會開放的系統」,並指出建築師不應只關心單棟建築,而應主動參與都市設計。當時確實有這樣一股潮流。然而,篠原先生對於這樣的風潮持懷疑態度,並反其道而行,強調透過獨棟住宅設計這樣一種「封閉系統」的方式,來面對社會、與社會對峙。
如今回頭再讀這些論述,會感受到篠原先生這些主張,反而很直接、很有說服力地傳達了作為建築師的自覺與手感,令人印象深刻。

《白の家》提供=東京工業大学篠原研究室
為何仍持續保有當下性
坂牛──這本書至今仍具有當下性的理由之一,或許就在於「白之家」經常成為學生課題的一部分。能夠被這麼多人持續閱讀,也許正是有這樣的背景在背後。
再進一步說的話,如今不只是日本,連美國、中國也都在關注篠原一男。不過,就算我們說「受到關注」,那也不代表是因為某個共同的評價標準才被注目。譬如他在2010年的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獲得特別紀念金獅獎,或是在海外有許多建築師粉絲,但若說大家都是基於同樣的興趣而關注他,我想恐怕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之前我曾受邀前往美國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參加一場篠原先生的展覽和相關座談。策展人是專研丹下健三的森·康恩(Sen Kuan),而他感興趣的重點似乎是關於建築師從城市轉向受限領域工作的時代,也就是篠原一男作為丹下以後的建築師的那個面向。展覽本身非常極簡,主要是將篠原先生住宅的原始圖紙平鋪在桌上展示。因此,現場並不是每個人都在高呼「篠原真厲害」的那種熱烈氣氛。
之後,我又去了在上海舉辦的篠原一男展覽,這次的展出無論在質量上都極為出色。那是由上海市政府主導,在當代藝術館中大規模舉辦的展覽,光是規模就有天壤之別。展出內容包括了像「未完之家」(1970)中庭空間的實體尺寸模型等,非常充實。東京工業大學的戴維·史都華(David Stewart)先生看遍世界各地的篠原展,也說這場是最棒的。觀展人數也相當驚人,平均一天有2000人,在為期60天的展期內累積高達12萬人次。若是在日本舉辦建築師展覽,大概只有這個數字的十分之一。甚至連當地的時尚雜誌也爭相報導,可見熱度之高。
該當代美術館的展場原本是亞洲最大的火力發電廠,於三、四年前改建開放。館方表示這是他們首次舉辦建築師個展,而這位建築師是日本人,也讓我感到相當神奇。我問了年僅三十多歲的館長為什麼選擇篠原一男,她回答說:「篠原一男的設計是邏輯性的,能夠用單一邏輯建構出完整的作品,這一點讓人著迷。」雖然不清楚她的興趣是否與那12萬名觀眾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是,這裡的關注與美國是不同的。
再說到國外的建築師,例如克里斯蒂安·凱雷茨(Christian Kerez)就是篠原的頭號粉絲。他被篠原那壓倒性的造型與空間吸引著,對他來說,大概邏輯是否一致並不重要。另一方面,我事務所裡年輕的員工裡也有人是篠原的愛好者,他說現在的日本建築師多半強調社會性與公共性,對這股潮流他已經感到厭倦了。現代的建築師整天搞什麼都市再生之類無形的東西,但對他來說,建築師最吸引人的就是那種能創造出酷炫空間的能力。我想,日本似乎有不少人正是被篠原一男這樣的魅力所吸引。
在這樣的背景下,《住宅論》所蘊含的箴言式語句,就成為了強而有力的後盾。舉例來說,在大學的課堂上做設計製圖時,大概不會有老師會說出「住宅越寬敞越好」這樣的話,也不太可能有老師會說「住宅就是藝術」。相反地,若是學生太過追求帥氣造型,老師反而會說「建築不是為了造型」,我自己也會這麼說(笑)。
南──如果說那些篠原的粉絲們是否真的親自去看過他的住宅呢?由於是住宅,自然有其限制,我想絕大多數人應該都只是透過照片看過吧。照片和模型。那麼也就是說,篠原的住宅作品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並不是因為它們作為「無可取代的空間體驗(かけがえのない空間体験)」——也就是「被親身經歷的空間(生きられた空間)」——所帶來的震撼力,而是在於它們作為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所展現出的強烈存在感與震撼力,是以一種鮮明的形式出現在人們面前。
坂牛──篠原先生的作品,大家不都常拿來當作學校課題,讓學生製作模型嗎?像小嶋一浩先生,據說他一開始也是讓學生製作篠原的建築模型。他說只要是篠原的作品,選哪一件都可以。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篠原的作品沒有失手之作。
天內──好像幾年前,在桑澤設計研究所(桑沢デザイン研究所)也曾舉辦過一場只展出篠原住宅模型的展覽吧。
社會性的身體動作
南──回到書籍的話題,最看似積極介入社會的建築家代表,莫過於黑川紀章了。他那麼早就出道、活躍於媒體,站在左翼立場發言,又在牽引代謝派(Metabolism)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就這層意義而言,沒有人能比得上黑川先生。然而,如果說黑川先生的書是否被廣泛深入地閱讀過,那就有些可疑了。
不過,篠原先生的書的確是被認真讀過的。從《住宅論》出版至今已超過四十年,即使在當下閱讀,依然具有堅實的強度。我認為,這樣的強度,甚至在一百年後讀來也依然成立。換句話說,不論是住宅論也好、建築論也罷,要寫出超越這本書的內容是極為困難的。因為其中有許多誰都說不出口的格言式語句被果斷地拋出來,於是也就無話可說了。大家在設計住宅或建築時,都會說「社會性很重要」或「要考慮都市的脈絡」,但正因為人人都能說,反而可以說那是放棄思考的話語。如果我們試著去排除這些話語,思考最後究竟會剩下什麼,那麼這本書所寫下的內容,便會讓人聯想到數學的公理一般的東西。
建築界經常會說「建築物還是要親自去現場看才知道好不好」。但若反過來問:為什麼非得親自去看不可?恐怕大多數人都無法作答。因此我反而避免說那樣的話。我想說的是,也許不需要去現場也能理解的建築,才是最厲害的。三島由紀夫曾說過:「實地採訪寫出來的文章當然不容易,但最厲害的是即便沒去現場也能描寫出來的人」。我想,篠原建築之所以能如此廣為流通,也與此有關。也就是說,即便沒去現場,也能吸引人的魅力,就存在於篠原的建築之中。而他做到這一點的媒介,還是住宅——這種極為局部性的、理應非得進入內部才能理解的類型。篠原先生曾說:「住宅的內部空間是自由的(住宅というのは内部空間は自由だ)」。即便如此,他仍然持續獲得那些未曾實地前往的人們的壓倒性支持——仔細想來,這是件相當了不起的事。
坂牛──我想建築家們或許都希望自己也能說出像《住宅論》裡那些極端的格言語句。雖然內心這麼想,但往往因為自身的立場或害怕被批評缺乏社會性而不敢說出口。可是篠原先生卻說得出口。或許這也和他曾是數學家有關。而且,他還是在身為大學教授的情況下,將這些話具體寫成了文章。正因為這些話是大家都想說卻說不出口的話,所以這本書才能歷久彌新、長年被閱讀吧。
我自己也曾在高中時期讀過黑川紀章的《Homo Movensis:城市與人類的未來(ホモ・モーベンス──都市と人間の未来)》,讀完非常感動,甚至想成為像黑川那樣的人。不過,我想現在再讀,大概不會再有那樣的感動了。可是《住宅論》卻不同,例如至今我仍會想著:「像那種寬廣到看不到對面牆的住宅,好想有生之年造一棟看看啊(笑)」。這本《住宅論》確實是能夠直接打動建築家的本性的一本書。
南──儘管這本書完全沒有展現出「社會性的身體動作」,但卻能在任何時代持續被閱讀、持續展現語言的力量,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或許反而擁有極為深刻的社會意義也說不定。
南──篠原先生在研究室也曾進行過民宅調查或類似設計調查(Design Survey)的活動吧?可能也承襲了當時伯納德・魯多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那一脈的流風。坂牛先生您當時在研究室時,研究室主要是在進行什麼樣的工作呢?
坂牛──我是在1980年代屬於篠原研究室的,那時候已經沒有再做民宅調查了。我認為,關於民宅調查的部分,已經以「民家就像蘑菇一般(民家はキノコである)」這樣的結論畫下句點。像《住宅論》也正是從日本傳統樣式建築的討論開始的吧。會做民宅調查,應該是出於想要了解日本傳統的動機吧。再加上,如「藤村紀念堂」(1947)那樣的谷口吉郎先生的作品,應該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篠原先生在東京工業大學擔任清家清先生的助手時,谷口先生還在校內。關於谷口先生的話題在研究室偶爾也會出現,但據說幾乎沒什麼機會交談,是個如雲端般高不可攀的存在。
南──人變老之後回歸傳統,這點是可以理解的,但篠原先生的情況有趣的是,他是從傳統出發,反而變得愈來愈激進。他逐一拆解像是深遠的屋簷與軸組這類日本傳統建築的空間語法,逐步豎立起女兒牆,建築轉化為立方體,抽象性也隨之提升。到了後期,像是「東京工業大學百年紀念館」或「橫濱港大棧橋國際客船航站」的競圖案,作品變得極度抽象。那麼這樣的方向,是一開始就抱持著這樣的意圖呢?還是說在設計過程中逐漸演變而來的?
坂牛──篠原先生原本在東京物理學校(現東京理科大學)主修數學,後來因為喜歡清家先生的作品,才進入東京工業大學。清家先生是將日本傳統現代化的建築家,或許篠原先生也想要繼承這樣的風格。但當他思考要以不同於清家的方式解構傳統時,便出現了「象徵性」這個概念。他在《住宅建築》一書中有詳細記述,例如「狛江之家」(1960)那張合板天花板,還有「傘之家」那張合掌構造的張力,被他視為日本傳統空間的暗喻。他寫道:「當抽象空間與這種精神構造互相交融時產生的東西,我稱之為象徵空間(抽象空間がこのような精神構造と交換しながら進むときに生まれてくるものを私は象徴空間と呼ぼう)」。
篠原老師是有意識地切換自己的建築風格,這種方法論有點像畢卡索。他在《住宅論》中提到所謂的「第四空間(第四の空間)」。他說自己最終想要創造的就是「第四空間」,但那個時候還看不清楚,因此他邊摸索邊從傳統出發。後來在某個時期,他徹底轉向,提出了「龜裂空間」這個主題,轉化為像「未完之家」與「篠之家」(1970)那樣的系列。
然而,那股流向後來也再次出現變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原通的住宅」(1976)。那件作品採取了將異質物件接合的方式,我想從那個時期開始,他心中或許開始感受到「混沌(chaos)」的存在。像這樣,在我心中,篠原先生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建築的流行
天內──篠原先生對於「混沌(カオス)」的理解,是純粹來自數學上的混沌理論嗎?
坂牛──也許根本上有那樣的背景,但我認為他所說的「混沌」是更一般性的意涵。不過,會注意到「混沌」這一點,本身還是讓人覺得他畢竟是位數學者。
天內──剛才您提到坂本先生說篠原先生是「詩人」,那麼,是否可以理解為,對於那些無法僅以理性來解釋的部分,篠原先生重新命名為「混沌」呢?
坂牛──這也是其中之一,不過那個時期的篠原先生,其實經常出國旅行。他對里斯本的印象,在《住宅論》中也有提到。他說里斯本是非常美麗的城市。那個時候,他可能就產生了「那相較之下,東京是什麼樣子呢」的想法。接著,他又去了非洲,在那裡親眼見到混亂無序的城市樣貌,或許也因此覺得:「既然如此,那東京應該也還算不錯吧」。我想,他會開始關注「混沌」,大概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之下。
我曾經有一次機會看過篠原先生放映的非洲幻燈片。他沒有做任何解說,只是一張張映出幻燈片。但那時候,我依稀感受到他從非洲獲得的印象,例如「隨機性」、「缺乏連續性」等。我想他在其中感受到某種美感,而且那美感也與日本有共通之處。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日本是個缺乏秩序、相當骯髒的地方。但那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現實,如果無法在其中找到美感,就無法生存下去。我認為他大概是在思考這樣的問題。
南──東京本身就具有雙重性。道路乾淨、交通準時,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受控的都市之一。同樣地,我認為篠原先生的建築也在混沌中展現出一種乾淨的「設置(しつらえ)」感。就算只是從照片來看,篠原先生的建築也非常乾淨俐落。就連其中擺放的家具,也都井然有序,讓人彷彿看到能舞台一般的印象。那種看似不屬於現實世界的虛構感,卻又真實地以住宅形式存在,這樣的力量讓人感到震撼。而且,它還位於東京這樣的都市當中,這層現實感又更增添了震撼力。在如同垃圾堆般的混沌中存在著設置精緻的空間,這件事本身就是對都市的一種詮釋。我認為,那裡表現出了東京的雙重性。
坂牛──您說得很對。雖然篠原先生以「混沌」作為概念,但實際走進他的建築時,卻發現那空間非常乾淨利落,完全不是混亂的樣子。換句話說,那是一種非常排他的空間製作方式,將一切雜亂的東西都排除在外。篠原先生的建築正是這樣地充滿矛盾。
另一方面,像坂本先生與伊東先生,某個時期以後則開始試圖去包容更多東西,也就是採取更加包容(inclusive)的空間製作方式。例如坂本先生在打造自宅「House SA」(1999)時,特地在擺好家具後再拍攝照片,並刊登於《住宅特集》發表。他刻意展現出空間內各種雜物並陳的模樣,想強調那是個即使什麼東西進來都沒關係的空間。這樣的空間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混沌」,但還不到那個程度。這樣說或許有點武斷,但就繪圖來看,反而是近年石上純也的作品更接近真正的混沌。那樣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混沌」,而篠原先生所做的則仍帶有「過程中」的感覺,不是嗎?
南──沒錯,我很能理解。從現代主義建築的脈絡來看,我認為其中存在著「封閉/開放」與「沉重/輕盈」這兩組對立問題。以前我曾和伊丹潤先生談過這個問題,他說自己是屬於白井晟一的系譜,也就是「沉重建築」一派,不屬於如現代主義那般「輕盈建築」的脈絡。
回到篠原先生身上,我覺得他有種跳脫出「封閉/開放」與「沉重/輕盈」這兩個軸線之外的位置。他的作品雖然讓人感受到一種被圍起來的空間,但因為空間太過寬廣,反而不會讓人覺得是封閉的。如果作為理念來說,若有一種「連對面都無法看見」的住宅,那樣的空間便不會讓人有封閉感。我想,我們會一直被篠原先生的建築所吸引,或許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特性。相對而言,那些看起來「非常向社會敞開」的建築,反而會讓人覺得容易被消費、消逝。
坂牛──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當我們用某種評價軸來衡量建築時,如果那個評價軸擺動得過於極端,那樣的建築就會迅速被消費掉。以「沉重/輕盈」來說,像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那樣物質感很強的建築,就會讓人覺得很「沉重」。但在不久之前,「輕盈的建築」卻是主流。藝術其實就是在「沉重」與「輕盈」之間不斷來回擺盪。而且,這樣的週期也越來越短。
比如說,這是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曾提出的一個看法,他認為「扭曲彎曲的建築(グニャグニャした)」大約每四十年就會出現一次。像是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埃羅・沙里寧(Eero Saarinen),還有像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這樣的解構主義者等。現在則是既有像蓋瑞那樣的建築,也有方正的建築,可以說是處於混雜的狀態。而在這之中,也有一些建築似乎既不偏向任何一邊,也許篠原一男就是屬於那樣的一個流派。
我和天內先生曾一起參與翻譯的一本書,是傑佛瑞・史考特(Geoffrey Scott)於1914年所寫的《人間主義的建築──對歷史趣味的考察》。簡單來說,這是一本讚揚文藝復興的著作,但其讚揚的方式非常有趣。當時不屬於文藝復興脈絡的建築主要是新哥德風格,而這本書就是透過逐一論證,指出用來評價這些新哥德建築的理論有多麼薄弱。像是機械論的謬誤、浪漫主義的謬誤、生物論的謬誤等,逐一擊破。經過這一番批判後,他最終提出,建築若是用那些對建築來說是外在的問題系去構築,是行不通的,必須依據建築內在的問題系來創造,因而轉而讚揚文藝復興。

傑佛瑞・史考特(ジェフリー・スコット)《人間主義的建築──對歷史趣味的考察(人間主義の建築──趣味の歴史をめぐる一考察)》(鹿島出版會,2011,原著=1914)
大衛・沃特金(デヴィッド・ワトキン)《道德性與建築(モラリティと建築)》(鹿島出版會,1981,原著=1977)
1977年所寫的大衛・沃特金(David Watkin)《道德性與建築》,從由傑佛瑞・史考特撰寫序言這點就可以看出,它其實是對《人間主義的建築》的某種重製。建築,尤其是現代主義建築,是由功能、合理性、時代感等建築的外在因素所構成,但沃特金則主張建築不應只是那樣的東西。然而,這本書也可以說成為了後現代主義的讚歌式理論之一。
基於上述脈絡來看,這本《住宅論》可說是極為內在性地所寫的著作,可以說是繼承了史考特與沃特金的理論系譜。甚至可以稱之為在以建築內在性為核心的理論系譜中之「極北」之書。本書中有一種強烈的力量,會讓人相信「這是從人內心深處湧現的東西,你一定也會產生共鳴吧」。
南──確實如此。書中所提出的那些警語性的斷言(Aphorism),不但讓人感到震撼,某種程度上也會引起眾人的共鳴,這反過來也讓人感到一絲恐懼。二十世紀曾出現過未來派、立體主義等許多「主義」(ism)。那些作品都是伴隨著理論一同創作出來的,但幾乎都壽命短暫。最短的存在兩、三年,即使長一點也不過十年,這些「主義」作為短命的運動出現後又迅速消失。
我認為,理論並不是某種靜態的存在,然後依據它來創作作品這麼簡單。身處創作過程中的人,也可能抱持著理論性的態度。甚至可以極端地說,即使不發出語言,也能展現出理論性。例如,就算存在一套名為代謝派(Metabolism)的理論,也不能說只要遵從它就什麼都能做得出來。真正的理論性,是指站在極端點思考、自己去創造的行為。像篠原先生那樣,就給人一種笛卡兒、康德式的理論性:自己徹底地思考後再發出言語。也正因如此,他的話語才能經得起反覆閱讀。
我最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建築理論研究」中讀過的幾本書,每次讀的時候,我都會告訴自己:「這將是最後一次讀這本書,我不要再碰它第二次」。因為我不想太深地認同它,不想被它帶著走。康德的書就另當別論了,但像《住宅論》這樣的書,我覺得一生讀兩次就夠了。第一次是為了在自己內部孕育出那套理論,第二次則是為了「殺死」它。我現在甚至覺得,除非像這樣極端地看待它,否則就無法與它共處。
天內──像「主義」不斷變換的時代,這樣的傾向尤其明顯。有時我們會認為,只要有某個思想或命題,照著它去實體化就能做出作品。但其實建築理論大多是在事後回顧時才被整理出來的,基本上是隨著每次建築實踐而被不斷改寫的暫時性存在。
南──坂牛先生您自己也出版過《建築的規則──創造與解讀現代建築的可能性》這本理論書,您又是如何看待「建築理論」的呢?
坂牛──我在博士論文《關於建築設計中的意匠設計原理之研究──作為內含多樣性與可替代性的設計原理之設計指標的提案》中,試圖探討人們在進行建築設計時,不得不去思考的建築基礎原理。勒・柯比意有五大原則,而我則提出了九個。不過,這篇論文完成於2006年,科學論文往往在發表一年左右就會被新的理論所取代,因此我也在論文中寫道:本論文的內容只適用於2006年,若未來失效了就請用新的理論來取代它。我認為這樣的「暫定性」是必要的。後來香山壽夫先生對我說,這篇論文中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你提到的暫定性,我聽到後內心頗有「知我者言」的感慨(笑)。
南──這段話非常具有啟發性。暫定性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與篠原先生截然相反的態度。換句話說,暫定性是一種修正主義,但許多理論其實正是透過修正主義而建立起來的。即使是相對論也一樣,像是特殊相對論被修正之後才有了廣義相對論。也就是說,理論本質上就包含了不斷被修正的層面。
天內──在哲學中,這種修正主義有時不見得被正面看待,但在美學領域中,它則常被視為一種比較靈活應變(ad hoc)的態度。這是因為所追尋的作品總是不斷地持續被更新,總是處於最新狀態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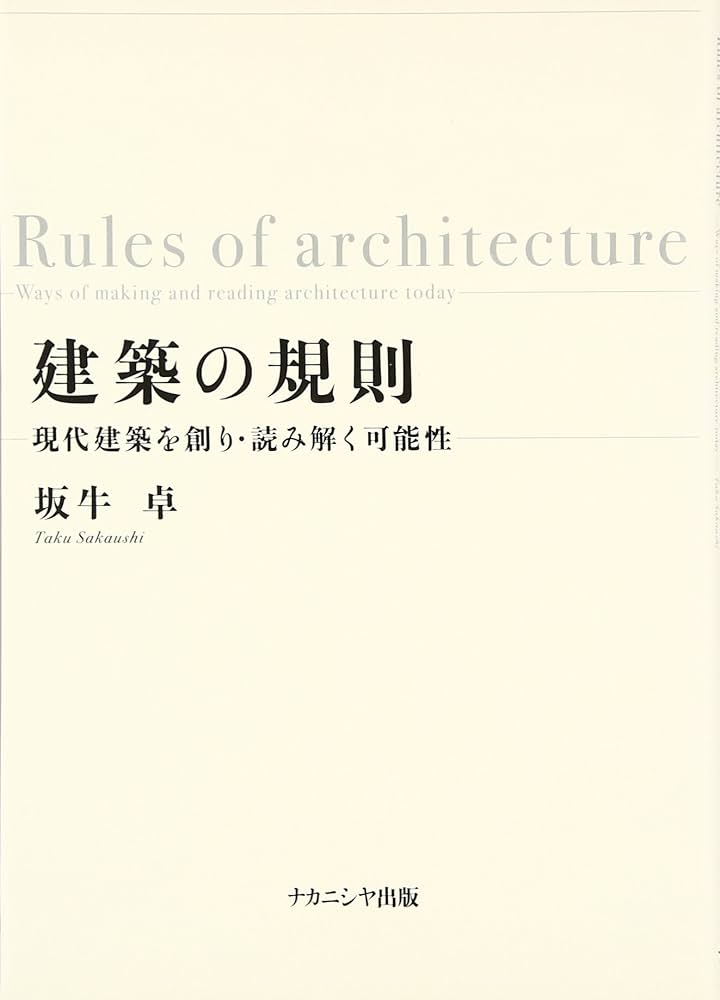
坂牛卓《建築的規則──現代建築的創作與解讀的可能性(建築の規則──現代建築を創り・読み解く可能性)》(ナカニシヤ出版,2008)
坂牛──南先生曾將《住宅論》比擬為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稱之為「純粹建築批判」,我對此非常能理解。《純粹理性批判》是討論人類理性的界限的著作。它主張從現在開始是人類的時代,但同時指出人類的能力只能及於某個範圍之內。照這個觀點來看,《住宅論》也可以說是在探討建築究竟具有多少能力的著作。與康德一樣,它在論述真理。也正因如此,這本書才能歷久彌新,始終值得一讀。
南──在建築理論當中,往往會受到技術革新的影響。舉例來說,勒・柯比意在設備方面,其實可以說是屢屢失敗。他的確有可以稱為修正主義者的一面,總是把失敗悄悄掩飾掉,或者換個形式呈現,不斷地進行修正。
坂牛──《住宅論》中完全沒有提及技術方面的內容。
南──是的。就這層意義來說,這本書更像是一本哲學書,試圖確立「悟性」的界限。它試圖去除與建築相關的各種技術與外在狀況,進行還原後,再來思考「關於新的建築可能性,我們能思索些什麼」,並且不藉由任何他者的援引,而是懷著覺悟徹底探究並貫徹這個命題。舉例來說,像是將住宅還原為「機能空間」、「裝飾空間」、「象徵空間」三種抽象空間,並由此試圖重新提出建築的可能性的〈三種原空間〉(《住宅論》p133〜p157),從中可以強烈感受到這樣的態度。沒有借助其他理論,也沒有試圖以權威加持,而是一行行僅以「我這樣思考」的表述來進行論述。因此,每一句話都能讓人感受到「他是在說自己的事」。
坂牛──篠原先生總是要求我們寫作時必須使用主語「我」。我畢業後和他一起編了一本書《經由篠原一男 東京出發的東京論》(鹿島出版會,2001),當時我用「我們」來寫,他就說要改成「我」。他說那樣寫才是建築家的文章。他也許是想說,應該要以接近客觀真理的層次來書寫。
南──理論書中的主語問題確實很值得思考。像是雷姆・庫哈斯的書就是由寫手代筆,所以讀起來會覺得主語不明,說話者是誰很難辨識。相對地,阿爾多・羅西的《都市與建築》(大龍堂書,1991)與《阿爾多・羅西自傳》(鹿島出版會,1984)則是像篠原先生那樣的風格,是以「我」為主語來書寫的,是「我」的故事。另一方面,槙文彥先生的《若隱若現的都市》(鹿島出版會,1980)因為是共著,所以又不同。整體來看,槙先生的書中可以感覺出他有意想抹去「我」這個主語的痕跡。建築師經常會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覺得必須與社會有所連結,因此一旦使用「我」,就容易被解讀為只是敘述某個極其私人的故事。在這種情況下,像篠原先生或羅西的書那樣,以「我」為書寫方式的作品反而能廣泛流通,這點非常有趣。在建築領域中,像是黑川紀章那樣,以「我們」的口吻來談論社會的書寫方式,似乎常常會成為一種免罪符。
天內──正如「新國立競技場」問題所象徵的那樣,「公共性」這個主題如今再次變得熱門起來。
南──除了「新國立競技場」之外,我覺得還有很多應該被關注的問題。前陣子我在澀谷散步時,發現大谷幸夫先生的「東京都兒童會館」(1964)已經被拆除了,我不禁懷疑是否有人發起過保存運動。「新國立競技場」問題反倒成了掩護其他建築物被悄悄拆除的遮羞布,這才是更該被關注的問題吧。
坂牛──我也這麼覺得。前陣子見到坂本先生,他說:「我雖然會大聲疾呼,但現在社會性與公共性的過度強調實在太誇張了。」他認為「只要主張社會性與公共性,就彷彿所有價值都可以被相對化,甚至變成免罪符,這種風氣是很不對的。」我相信坂本先生本身當然也十分重視社會性與公共性,但也許是因為311之後,他認為這股趨勢已經走得太遠了。
當代「住宅論」的可能性
南──《住宅論》這本書,就像是把數學中的形式化套用到住宅上的書,也可以說是一部「住宅基礎論」。書中並沒有提及設計上的細節。如同坂牛先生剛剛所指出的,書中也完全沒有涉及技術問題。本書中雖然使用了「基本空間(プライマリー・スペース)」這個說法,但其實是將各種元素削減到最低限度後所保留下來的「基本」概念,並以此作為住宅的基礎來進行思考。正因如此,一方面本書擁有至今仍未褪色的面向,另一方面也無可否認這是四、五十年前所寫的情境論。以日本的脈絡來看,進入2010年代中期,住宅過度供給,空屋情況顯著,即便想建也很難建。而且如前所述,在各種媒體資訊氾濫的今天,一張照片所帶來的衝擊力也變得薄弱了。在這樣的情境下,我想思考的是,如今若將《住宅論》字面地作為一部住宅論來細讀,它會具有怎樣的意義呢?
天內──雖然會有些重複,但篠原先生在《住宅論》的出發點是以「傳統」和「民眾」等主題為核心,並從中試圖發展出一種樣式。回顧大正時代,建築師也熱衷於創造樣式,篠原先生同樣也在嘗試建立自己的樣式。然而,坦白說,如今「創造樣式」這樣的態度究竟有多大的效力,我其實並不太確定。
坂牛──在《住宅論》中,篠原先生提出了「三種原空間」,但現在連「空間」這個概念本身,都有些過時了。至於樣式更是不用說。這不只限於建築,比如小說等其他領域,如今的寫作趨勢反而是「如何消除風格」。因為只要有風格,就會固定某個時代。因此,在這種什麼都有的時代裡,風格已經不再具有意義。從這個角度看,《住宅論》一書中雖有可共鳴之處,但同時也具有作為反面教材的一面。篠原先生常說:「要思考與大家所想的不同之事,並徹底思考其有效性。」在現代主義盛行的時代,他提出傳統,自己也是這樣實踐的。他是將這樣的思維作為一種策略來執行的。時代總是不斷推陳出新,在時代轉折之際,採取這種態度來深入思考是很重要的。
南──原來如此。讀這本書時,我有種印象,彷彿隱隱存在著一位看不見的假想敵。不用說是戰後的「最小限住宅」,還有現代主義、機能主義、新陳代謝建築、預製建築產業等,所有一切似乎都被假設為對立面。我當年撰寫《住居如何可能──極限都市的住居論》(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時,也讀了許多不同的住宅論,但在篠原先生的《住宅論》之後,很難再找到可與之比肩的作品。在此之前,例如池邊陽先生或吉阪隆正先生等,都是以戰後住宅不足這種社會背景為前提,寫出近乎訴狀般的切實住宅論;然而自篠原先生之後,似乎就很難再出現經典的住居論。
坂牛──是的,如果只侷限在住宅領域的話,幾乎沒有可稱之為經典的作品了。
南──雖然磯崎先生的《栖十二》(住まいの圖書館出版局,1999)也可以算是一部住居論,但那也是一部關於古老住宅的選集而已。
天內──那麼,隈研吾先生的《10宅論──10種類的日本人住的10種類住宅》(トーソー出版,1986)怎麼看呢?

左=《栖十二》(住まいの図書館出版局、1999)
右=《10宅論──10種日本人居住的10種住宅(10宅論──10種類の日本人が住む10種類の住宅)》(トーソー出版、1986)
南──《10宅論》也是關於十個住宅的選集吧。若不是自作解說,也不是選集的形式,住宅論似乎很難成立。昨天在「戰後日本住宅傳說」展的開幕致詞上,美術館館長建畠晢先生也提到,展覽中的許多住宅,其實是建築師的自宅。像是丹下健三邸(1953)、原廣司邸(1974)、菊竹清訓的「Sky House(空中住宅)」(1958)、白井晟一的「虛白庵」(1970)、東孝光的「塔之屋」(1966),再到毛綱毅曠的「反住器」(1972)與伊東先生的「White U(中野本町之家)」(1976),這些住宅都是為家人或親戚所建,因此也可說是半自宅。自宅意味著業主=建築師,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自宅的多樣性也顯示出,在其他路徑上實現住宅建設的困難。1950年代到1970年代之間,許多建築師創作出名留青史的住宅作品,這些住宅一方面受當時高度經濟成長與都市化動能的直接影響,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些住宅試圖與時代對峙並建立連結。但若建築師要在非自宅的狀況下,透過住宅這個回路來消化這些問題,並回應社會,或許反而更為困難。因為身處於當中,反而更難以對其進行相對化的思考。
「作為批評的住宅」這個說法,至今也曾以各種方式由許多建築師提出過。即便朝著這樣的地平前進,在真正說出口前,就已被現實壓抑,甚至有種在與世界對抗時敗下陣來的感覺。若真是如此,那麼建築師的自宅就是這樣一條,能夠發聲進行批評的稀少回路之一。
從這個觀點來看,許多建築師的自宅,都具有極為簡潔且具力量的形式性與訊息性,至今仍維持著不減的強度。
坂牛──坂本先生的「水無瀨的町家」(1970)也是為他姊姊所建。相比之下,篠原先生的「白之家」等作品則不同。篠原先生的弟子們總是異口同聲地說:「老師真是很幸運,遇到了很棒的業主們啊。」(笑)每當有人這麼說時,篠原先生總是會否定:「哪有這回事。」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幾乎每一位業主都是採取「請隨你所好設計」這樣的態度吧。
南──不過據說他晚年時曾說:「我討厭被業主牽著鼻子走,所以不想再接住宅設計案了。」
坂牛──那時的業主傾向或許已經有所改變了吧。不過在1960到70年代之間,的確是相當幸運的時期,很多業主是大學教授、藝術家,或者對藝術有高度理解的人。正因為如此,才能做出各種大膽的嘗試。
天內──畫家中村正義就是「直方體之森(中村正義美術館)」(1971)的業主,他曾與所屬的日本畫組織鬧翻,並自行創立組織展開活動。就與主流保持距離的姿態來看,他或許與篠原先生有某種共通之處吧。
獨立/包容 Exclusive/Inclusive
坂牛──在上海舉辦的篠原一男展覽開幕時,好像舉行了一場由長谷川逸子、伊東(豊雄)與坂本三位出席的座談會。據說在那場座談會上,當談到篠原住宅的最高傑作是什麼時,坂本說他與伊東的意見不謀而合。於是我問他們認為是哪一件作品,答案是「土間之家」(1963)。一般來說,若談到篠原住宅的最高傑作,大多會提到「白之家」或「上原通的住宅」,但他們卻認為「土間之家」更為出色。雖然我不清楚兩人為何如此評價,但在普遍被認為毫無生活氣息的篠原住宅中,「土間之家」卻是仿照傳統日本農家打造的,因此反而散發著生活氣息。篠原的住宅通常都規劃得非常精緻,連家具也只擺放自己挑選或自己委託家具設計師設計的作品,可說是徹底到極致。相對而言,「土間之家」是一個容納什麼都可以的空間。或許正因如此,他們才會覺得這樣的空間與自己所追求的更為接近。

「上原通之住宅」 攝影=多木浩二
『2G(No.58/59 篠原一男)』(G.G、2011)
南──確實,很難想像篠原的空間裡擺滿了物品的樣子。
坂牛──《2G(No.58/59 篠原一男)》 2011年号 中的照片正好證明了這一點。那裡所刊登的照片全部是新拍攝的,如果是篠原尚在世時,這些照片絕對不會被公開。他不可能容忍照片中有人、擺著觀葉植物這樣的情況。如果要使用照片,他肯定會說應該用過去的照片才行。看著那些新拍的照片,我發覺,即使將篠原一男的建築視為被人生活過的住宅來看,也依然令人讚嘆。他原本試圖創造出被徹底排除、exclusive的空間,但像「地之家」(1966)這樣的建築,反而因為能夠容納各種事物而顯得更具魅力。從這個角度重新發掘篠原建築的另一面,這本書可說極具價值。
南──這真的很有意思。若從exclusive(排他)與inclusive(包容)來思考,會讓人聯想到勒・柯比意與洛斯的對比。不同於柯比意那種精心設計、整潔的空間,洛斯的住宅則充滿了各種家具,因此形成一種極其親密的空間。不過若說洛斯的空間缺乏形式性,也並不正確,兩者其實是並存的。聽了剛剛的話,我想到篠原的住宅或許也有這樣的可能性。儘管他的建築是以exclusive的方式構成,是抽象的,但同時也有成為實際生活空間的潛力。這樣的可能性確實令人興趣盎然。
坂牛──篠原曾進行過對民家的研究,因此像「土間之家」這樣的作品,是建基於農家傳統樣式之上。而即便是「地之家」,也讓人強烈感受到一種「土味」。雖然他曾用「裂縫的空間」來形容其建築,那會讓人聯想到白盒子那種銳利的空間,但其實從「地之家」的黑色鐵板、紅色壁紙,或是「篠先生之家」的金色壁紙來看,可以發現他其實對素材非常講究。

《土間の家》提供=東京工業大学篠原研究室(無断転載禁止)
天內──他是不是其實認為理論只佔其建築觀的一小部分?
坂牛──與其說是這樣,不如說他對於那些即使自己喜歡,但不符合其理論策略的東西,基本上是選擇不去書寫的。即使是勒・柯比意,他也用了各種顏色,但長期以來都沒有撰文談論色彩。據說他在編全集時,因為彩色印刷太昂貴而放棄,因此他也決定不再多談顏色的問題。但實際建築中,卻充滿了色彩。
他去世後,1997年出版了一本名為《Le Corbusier — Polychromie Architecturale》的彩色書籍,裡面有如《模度原理》那樣的色票帳,還收錄了他所設計的「薩爾布拉系列」彩色壁紙,並附上他所撰寫的色彩相關文字。但這些文章至今未被翻譯,幾乎未曾流通。那是因為他非常重視媒體,因此對那些無法透過媒體強烈傳達的事物選擇不去談。我認為篠原也有這樣的傾向,像色彩或素材這類無法透過媒體產生強烈訴求的內容,就不會納入其建築概念中。我想,這是他們的一種策略。
南──表面上看來幾乎反社會的強烈格言、具有無與倫比強度與形式性的抽象幾何住宅群、以及對表現流通的精密策略——這些可說是作為建築家的篠原先生為人所熟知的特徵。但事實上,他對於鄉土文化的注視、多彩的色彩感受、對素材的關注,以及帶有包容氣息的氛圍等,這些看似站在抽象對立面的具體感性,其實也都能從篠原的建築中發現,這樣的觀點實在耐人尋味。
篠原的《住宅論》作為眾多建築書籍中極為特殊的超級長銷書,至今仍持續被閱讀,幾乎可以說是發揮著「聖經」般的功能。今後的日本,將迎來「不再蓋建築的時代」,在「住宅建築」的語境中,社會也將進入另一個次元。但「住宅」這一問題本身,仍將根據社會的轉變而不斷被重新提出。於是,我們就不得不思考:這本半個世紀前寫成的書,至今還能提供什麼樣的啟示?又或者,我們是否該準備與這本書集體道別了呢?這都是我們需要各自深思的問題。
[2014年7月6日,於LIXIL:銀座]
坂牛卓(Sakaushi Taku)
1959年生,建築師,O.F.D.A.共同主持人,東京理科大學教授。主要作品包括:「幸草園(クローバー学園)」、「神田明神旁的辦公室(神田明神脇のオフィス)」、「愛麗絲與特雷斯(アリスとテレス)」、「內之家(内の家)」等。著有:《言語與建築(言葉と建築)》(與人合譯)、《建築的規則──創造與解讀現代建築的可能性(建築の規則──現代建築を創り・読み解く可能性)》、與塚本由晴合著的《α空間──塚本由晴與坂牛卓的素描檢查(αスペース──塚本由晴・坂牛卓のエスキスチェック)》等。
南泰裕(Minami Yasuhiro)
1967年生,建築師,Atelier Ampelux主持人,國士館大學教授。主要作品包括:「PARK HOUSE」(2002)、「spin off」(2007)、「坎特雷工作室(アトリエ・カンテレ)」(2012)等。著有:《住居如何成為可能(住居はいかに可能か)》(2002)、《Traverse(トラヴァース)》(2006)、《建築的還原(建築の還元)》(2011)等。
天內大樹(Amanai Daiki)
1980年生,研究領域為美學、藝術學與建築思想史。現任靜岡文化藝術大學設計學部講師。合著有:《Disposition(ディスポジション)》(2008)、《建築・都市書目導覽21世紀(建築・都市ブックガイド21世紀)》(2010)等。



留言
張貼留言